2012年9月16日,中國(guó)當(dāng)代著名雕塑家景育民先生的當(dāng)代公共藝術(shù)作品《行囊》在長(zhǎng)春凈月國(guó)際雕塑公園落成,正式開(kāi)啟了這件作品的藝術(shù)旅程。在作品《行囊》中,藝術(shù)家以對(duì)公共藝術(shù)的全新理解,融入了當(dāng)代城市發(fā)展理念以及對(duì)人類文化進(jìn)程的美好訴求,進(jìn)而呈現(xiàn)了當(dāng)代公共藝術(shù)的學(xué)術(shù)追求與審美價(jià)值。當(dāng)代公共藝術(shù)的發(fā)展不僅僅局限于本體語(yǔ)言、概念的拓展與演進(jìn),其靈魂更映現(xiàn)著所處時(shí)代的主流精神與社會(huì)集體的心理訴求。其思考的核心已經(jīng)轉(zhuǎn)向到對(duì)當(dāng)代人所處環(huán)境與生存狀態(tài)。

這種思考源于城市工業(yè)化所帶來(lái)的盲動(dòng)而導(dǎo)致的人類與生態(tài)之間的失衡與矛盾,進(jìn)而在此種狀態(tài)下人們呈現(xiàn)出的一種從工業(yè)文明時(shí)代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愚昧中覺(jué)醒的態(tài)度——開(kāi)始審視自我,開(kāi)始自律:如何改進(jìn)人類的生存方式,改變?nèi)藢?duì)自然的態(tài)度,自覺(jué)地放棄人對(duì)自然的輕慢與貪婪,而達(dá)到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讓生態(tài)理念成為自覺(jué)與需要。正是基于這種思考,藝術(shù)家以樸素的東方式人文關(guān)懷,從“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中汲取探索,在《行囊》的創(chuàng)作中著力闡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的動(dòng)態(tài)關(guān)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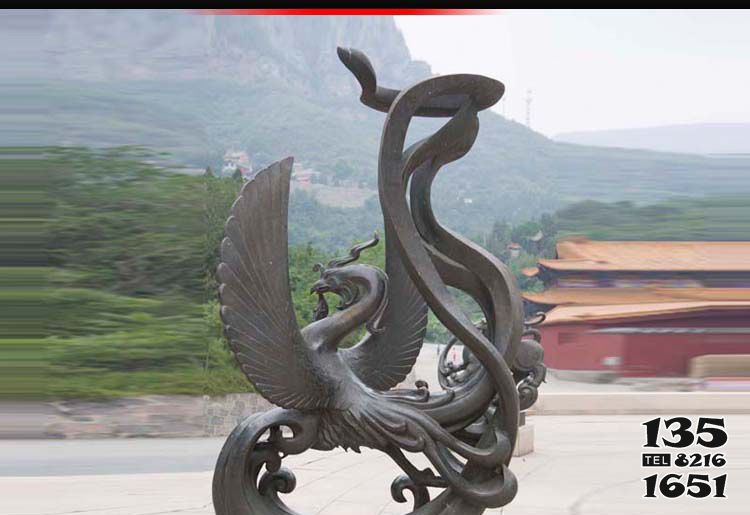
公共藝術(shù)作品《行囊》以超寫實(shí)的手法,將一只時(shí)尚的皮包“放大”成為不銹鋼的公共藝術(shù)作品置于公共環(huán)境的綠地中,以不同城市的代表性花草從“綻開(kāi)的拉鎖”中生長(zhǎng)。從直觀的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來(lái)看這件作品采取了“放大”的修辭方式,然而這絕不同于奧登伯格的日常品“放大”所追求的特殊視角與視覺(jué)效應(yīng)。作品《行囊》在貌似熟悉的面貌下,傳遞了兩個(gè)層面的關(guān)鍵信息:首先是“行動(dòng)的藝術(shù)”的觀念。行囊乃空包,可謂“容器”,它是“行走”的、“移動(dòng)”的。

每到一個(gè)城市都由該城市的市民將這個(gè)城市的土壤與花草培植到作品里,方構(gòu)成完整、有生命的作品,成為該城市的典藏,并承擔(dān)起日常的養(yǎng)護(hù)與澆灌。《行囊》在這個(gè)城市“駐足”之后會(huì)隨著其背后N個(gè)城市行走記錄的不斷添加而擴(kuò)展著作品的信息含量,它有別于傳統(tǒng)的定位方式,而以位移的狀態(tài)成為典型的“行動(dòng)的公共藝術(shù)”。其次,《行囊》采用了有機(jī)和無(wú)機(jī)相互結(jié)合的生長(zhǎng)雕塑的概念。“行囊”本身是由無(wú)機(jī)世界的不銹鋼構(gòu)成的,但是其內(nèi)部的土壤和植物卻是有機(jī)的生長(zhǎng)物質(zhì),這些花草隨著季節(jié)的變換進(jìn)入到生態(tài)輪回的狀態(tài)由旺盛到休眠到復(fù)蘇到返青再到熱烈的綻放,而《行囊》也體現(xiàn)了生命、時(shí)間的維度。

種植的過(guò)程則強(qiáng)調(diào)了人、藝術(shù)與自然的互動(dòng),人、藝術(shù)與城市的互動(dòng),人、藝術(shù)與時(shí)間的互動(dòng)。公共藝術(shù)作品《行囊》以“文化接力”的形式,以雕塑名城長(zhǎng)春作為起點(diǎn)開(kāi)始向國(guó)內(nèi)外多城市“行走”,不久將在中國(guó)蕪湖、中國(guó)北京、中國(guó)南昌、中國(guó)青島等地落成;這個(gè)“行走”的歷程還計(jì)劃延伸到國(guó)外,作品力求消解信仰、種族、宗教等意識(shí)形態(tài)的界限,進(jìn)而呈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的共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