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89年巴士底獄的風起云涌到柏林墻倒塌間的200年自成體系,對西歐文明、文化、藝術(shù)來講如此,對西方統(tǒng)治、國家主權(quán)以及帝國主義來講同樣如此。在現(xiàn)在的信息交流時代,東西方之間的原有力量平衡——“世界性政治”以及國際化資本主義正在被動搖,柏林墻倒塌前的1989年的北京,言論自由以及藝術(shù)自由的那些前提也已經(jīng)被改變。在這一年,學生占領(lǐng)天安門廣場,在此之前,此處的毛澤東像被破壞,而代以模仿紐約自由女神像的自由雕像。

對19世紀的歐洲移民來講,當他們航入紐約港時,正是自由女神像歡迎他們。電視傳播的1989年北京自由斗爭時時被全世界所關(guān)注,其中就包括挪威。中國的日常生活突然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兩種不同文化相遭遇。20年后的今天,我們發(fā)現(xiàn)以往的障礙正在被新格局所超越,這已在全球社會以及藝術(shù)王國的不同領(lǐng)域中顯現(xiàn)出來。在這方面,奧勒利斯勒魯?shù)率且晃凰囆g(shù)全球游歷者,他把東西方傳統(tǒng)融合在一起。

從早期孩童時代到接受不同大陸的學術(shù)、藝術(shù)教育,他一直固守此道,始終對區(qū)分“自律”藝術(shù)和實用設(shè)計的西方保守藝術(shù)教條充滿批判。以相同方式,他質(zhì)疑民族和地域偏見。這就是為什么在我們的世界性政治時期,他最終成為了“居家”者,因為他正把古老的手工藝傳統(tǒng)融入我們所處時代的科技之中。

他通過絲網(wǎng)印刷把攝影和數(shù)碼圖片轉(zhuǎn)印到瓷磚和瓷板上,隨后上面用畫筆手繪。他把古代形式、教義、圖畫以及象征符號融入自己的藝術(shù)世界中,把它們和當代媒體圖標、流行文化以及涂鴉并置在一起。從而,他把自己或者他人的建筑形式引入一層“陶質(zhì)”“皮膚”之中,成為“墻”或者“入口”。在全球范圍內(nèi)完成的20多個綜合方案中,利斯勒魯?shù)掠辛Φ卣故玖俗灾魏凸τ谩⒔ㄖ退囆g(shù)、圖畫和文本以及視覺和非視覺的區(qū)別是如何和永動過程中的時空相關(guān)聯(lián)的。

與其說把這些對比發(fā)展成為一種和諧的綜合,不如說舉例證明它永遠是一個問題——關(guān)于無限闡釋的問題的問題,這種無限闡釋的問題既不會被完全解決,也不會完全被封閉。讓我們看幾個例子,從而展示利斯勒魯?shù)率侨绾胃挥兴囆g(shù)性地利用這種張力的。就像觀念藝術(shù)家約瑟夫科蘇斯注定要創(chuàng)作商博良的紀念碑一樣,作為一位藝術(shù)家,奧勒利斯勒魯?shù)潞茏匀坏厝?chuàng)作伊瓦爾奧森的紀念碑。在其藝術(shù)生涯中,利斯勒魯?shù)率冀K關(guān)注記號、符號、書寫體系和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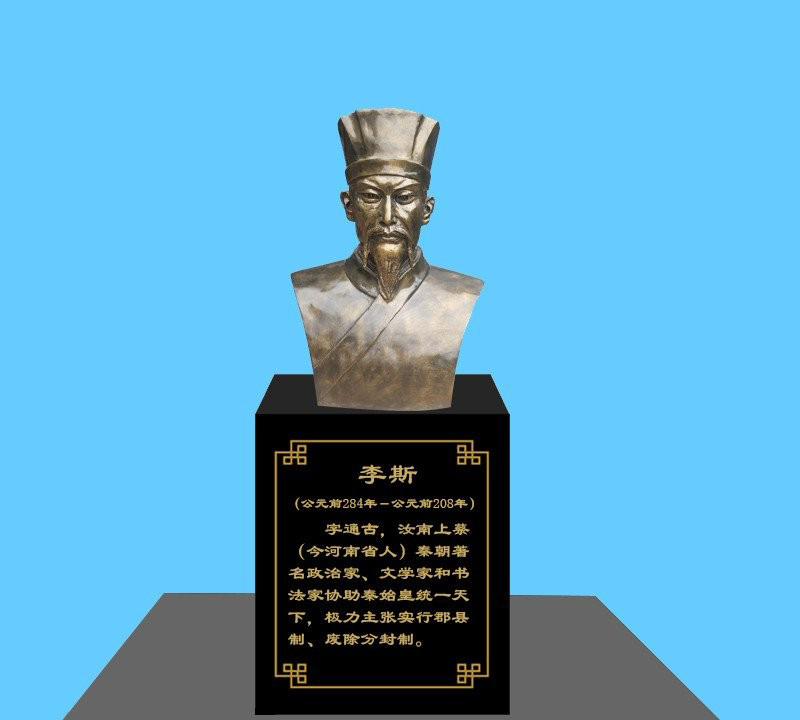
語言學家、抒情詩人伊瓦爾奧森在挪威方言多樣性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了一套全新的語言,至今仍是挪威媒體的日常用語。這種對語言的實際應(yīng)用就是利斯勒魯?shù)碌膭?chuàng)作方式,這種方式和他的兩個合作者異曲同工——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的建筑師斯維勒費恩以及作曲家阿爾納諾德海姆。三人使語言獲得了生命,語言不僅是音量、質(zhì)量、音質(zhì)、間歇與韻律,而且還是一種體驗,在其中視覺符號成為了可視的襯底,或者說是一種斷裂的音符,需要人們將它譜寫成曲。
利斯勒魯?shù)逻x擇玻璃墻,他用漢語、日語、阿拉伯語和希臘語在上面寫“有一千種語言”的語言片斷。于是,墻變成了透明屏風,觀眾在看到十米高的混凝土墻外的文字之前,可以透視這面墻。丹麥語、挪威語中常見的字母“”被放大、傾斜,變得即像一個超大的手寫符號,又像一個手寫記號;即熟知,又陌生。當利斯勒魯?shù)乱赃@種方式視覺化形象和基礎(chǔ),記號以及所描繪內(nèi)容之間的張力的時候,他同時激活了每一種語言體系作為一種編碼交流的環(huán)境,激活了一個作為對無限闡釋過程的對象。
《法律肖像》,位于奧斯陸法院大樓。涂鴉墻《上帝是女人》,位于奧斯陸大學神學院藝術(shù)的展出場所會影響觀眾對作品的接受。博物館作為一個庇護性場所,維護純粹的美學觀看方式。在公共機構(gòu)或者在戶外街道上展出,藝術(shù)便會和無數(shù)的其他闡釋相抵觸,比如說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闡釋等等。
奧勒利斯勒魯?shù)略谖鞣絻蓚€最具象征意義的機構(gòu)實施藝術(shù)方案,即奧斯陸法院大樓、奧斯陸大學神學院。他在法院大樓建造了兩根32米的柱子,高達9層,用2毫米厚的象征民主價值觀的書法式的圖案瓷磚覆蓋其表面,這些圖案很當代,他對比了穿長袍的穆斯林婦女和安迪沃霍爾在他的絲網(wǎng)版畫中所描繪的瑪麗蓮夢露。同類圖案不停重復,還有關(guān)于基督的圖像,旁邊并排文字,整個表面布滿長釘和筆觸式的涂鴉。“上帝是女人”的文字挑戰(zhàn)了當代闡釋,同時還有100多處其他文字,比如“上帝是黑人”、“基督教有太多的律師,太少的證人。
”“只有移動的人能感覺到鎖鏈”、“擴充學識的人助長了自己的痛苦”等等,橘黃色的交通標示則用來象征北愛爾蘭反對和平談判的獨立戰(zhàn)爭。在這里,奧勒利斯勒魯?shù)聫拿襟w世界中挑選出一段文字,從而展現(xiàn)對雷內(nèi)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變形,補充以巴巴拉克魯格的“你的身體是個戰(zhàn)場”,并重復使用克魯格的格言。這個主題展現(xiàn)了一張被分裂的婦女面孔,從而舉例說明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的差距。在這一作品系列中,理想化的洋娃娃與殘疾藝術(shù)家弗麗達卡洛的自畫像并置。
在這里,古代美人象征——波提切利的維納斯與穿體恤衫的美女并列,體恤衫上寫著“毫不驚奇于權(quán)力的濫用”。政治權(quán)利的使用,色情描寫的誤用,紐扣和身體、標語和禱告的出售。以這種方式,消費社會被作“好”或“壞”的陳述,以及我們?nèi)绾慰偸遣活檿r空地使用、消費、復制和再生產(chǎn)圖像和文字以及媒介世界中的藝術(shù)和庸俗作品。
這涉及到每個個體身體內(nèi)部的對比,就像徒勞無益的精神斗爭,在外部世界中無限的重復自我。以這種方式,奧勒利斯勒魯?shù)乱砸环N藝術(shù)時尚映射全球普遍存在的一種存在緯度:沒有誰能夠脫離資本以及交流而存在,而資本分配不均,交流又必須依靠資本。在2008年4月將在今日美術(shù)館展出的一些標題中,利斯勒魯?shù)轮苯又干鎰邮幍墓善笔袌觯热鐦祟}“華爾街的另一個不祥之日”、“金融時代”、“投資者激發(fā)政治投資者熱情”。從藝術(shù)方面講,在不停運動中,在光的恒動中,利斯勒魯?shù)陆Y(jié)合文字以及紋理制作出可觸表面,揭示這種永不休止的對比。
具體來講,他部分借助在同一版本《金融時代》的幾個復制品上畫畫,從而實現(xiàn)這一效果。在這里,他借助涂抹、隨意的筆觸,或者任由顏料滴灑和流動,從而召喚出一個強烈的陰郁世界。他重復使用黃色、紅色、藍色幾個基本色,制造出交織的、緊密的紋理,或者拋撒出隨機的線條,他夠使陶瓷表面作為雕刻般的浮雕獨立出來,或者將其覆蓋,從而賦予它一種繪畫效果。
使這些作品富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利斯勒魯?shù)略诿浇楹凸ぞ咧g、精神與手之間、藝術(shù)和手工之間、圖畫藝術(shù)和流行文化之間所進行的“不可能”的結(jié)合。這種“不可能”的結(jié)合也使利斯勒魯?shù)略谂餐钚聞?chuàng)作的的巨型公共作品頗具特色,即為奧斯陸的挪威工商聯(lián)合會總部創(chuàng)作的8層樓高的玻璃正立面。
當列奧納多的“飛行器”,瓦薩雷里的“光”以及勒泰斯瓦爾的“不可能形體”一齊擁向制圖板的時候,在科技的幫助下,這些體量和體塊被變形為真實的三維建筑形式和藝術(shù)形式,我們可以在畢爾巴鄂的格蒂博物館中看到,在利斯勒魯?shù)聻榘亓值莫q太博物館所作的創(chuàng)作看到,在他為巨型的新中央電視臺大樓所作的創(chuàng)作中也可以看到。新中央電視臺大樓由荷蘭大都會建筑師事務(wù)所設(shè)計,中國人、歐洲人組成的巨大團隊進行支持。
在某種程度上,利斯勒魯?shù)聻榕餐ど搪?lián)合會創(chuàng)作的“奔跑的柵欄”——《響應(yīng)》顯示了現(xiàn)象學上的、光學上的雙重挑戰(zhàn)。這件作品擁有龐大的、風狀的有機形式,步行者沿著它走,其與建筑表面形成對比,玻璃正面墻被以利斯勒魯?shù)碌牡湫惋L格處理過,所以當眼睛漫游者或者閑逛者路過的時候,會有不同的光學效果。利斯勒魯?shù)略诜鹕饺A夏國際文化廣場創(chuàng)作的《華夏拱門》可視為《大拱門》的相似版本,后者位于巴黎新區(qū)拉德芳斯,是一個樣式簡單但令人難忘的立方體,這是為紀念國際友誼而建立的一個帶空間的基地——既作為用于交流的博物館,又作為人權(quán)基地。
5米高、5米寬的鋼鐵入口與利斯勒魯?shù)庐斍白畛J褂玫牟馁|(zhì)體現(xiàn)了利斯勒魯?shù)碌乃囆g(shù)特征——在空間建筑形式和表面幻覺空間之間,在近視和遠視之間,在“浪蕩子”的反復無常和自制者的平靜安詳之間,在不同時代和文化之間,在一個全球政治時代,只有一位藝術(shù)全球游歷者才能夠?qū)崿F(xiàn)。





















